记者丨闫桂花
近日农夫山泉董事长钟睒睒喊话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一事引发关注。11月20日下午,这位前首富在江西赣州一场活动中呼吁抖音、今日头条,作为“有足够力量掌控舆论的平台企业”,“承担一个企业的文明准则和规则”,并喊话这两个平台及其实际控制人“不要以任何所谓‘避风港’原则进行搪塞,立即撤除对我的个人名誉权的侵害的言论、图片,并向我个人和我家属道歉”。“我在等待你们诚恳的道歉!我在等待。”
今年年初,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离世后,农夫山泉掌门人钟睒睒与哇哈哈的过往“恩怨”被网友翻出,之后农夫山泉又被指商品包装存在日本元素、其子拥有美国国籍等,舆论危机在民族情绪裹挟下持续加剧。在持续被“网暴”近180天后,农夫山泉的市值蒸发近2100亿港元;而持有农夫山泉近83%的股份的钟睒睒,个人财富也缩水近1800亿港币,其在今年10月的《胡润百富榜》上由此前的首富跌至第二,首富位置也由字节跳动总裁张一鸣所取代。
所谓的“避风港”原则是指平台作为空间服务提供者而不是内容生产者,在已履行了通知、删除等义务后就可以获得民事责任豁免。该原则起源于美国1998年制定的《数字千年版权法案》(DMCA),目的是在面临侵权等问题时,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一定程度的责任豁免。该条款已被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多数国家所接纳,成为互联网版权保护的核心规则。但如果平台明知或应知其服务对象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但未采取必要措施(如删除、屏蔽或断开链接),则需要与侵权者承担连带责任。
针对网络暴力,受害者可以选择诉诸法律,对加害者曝光隐私、捏造事实而污人清白、毁人名誉等行为进行惩罚,但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宏在《风声评论》上撰文指出,尽管惩戒之网已然很严密,被施暴者在诉诸法律救济时仍面临立案难、取证难、定损难等诸多难题。“在因虚拟性和匿名性导致的取证困难之外,‘法不责众’的事实也让网暴的惩戒一般只能针对直接的施害者而无法辐射至所有的推波助澜者。”
因此,至少眼下,当个体或特定群体面临不实信息侵扰乃至网暴时,很难全身而退或得到理应的公正。网暴、仇恨言论、谣言充斥公共舆论,背后一大原因是整个信息传递的过程已经发生了范式的变化,以往信息主要是借助公共媒体,借助受过职业训练的人来传播,但现在,平台直接打通了受众和信息之间的媒介,信息得以更快更便利传播,尤其是那些更极端、更情绪化、简单化归因的信息——而这正是不实信息和谣言产生的地方。

这也是为什么钟睒睒会选择公开诉诸媒体控诉,而不是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吊诡的是,他对“网暴”的反击,很大程度上也需要借助他所批判的平台的功能来实现,一旦没了首富或知名企业家的身份,拳头也只能打在棉花上)。
更大的问题在于,激发起用户情绪,无论是愤怒和仇恨,恰恰是平台盈利的重要模式。传播愤怒,远比传播其他信息更能提高流量和用户的参与度,正如2019年12月Facebook(脸书)内部流出的文件指出的那样,平台出于商业目的而刻意推动了“病毒式的传播”这种新事物,而根据他们的研究,“让人感到愤慨的内容与错误信息更有可能像病毒那样传播。” 赫拉利在新书《智人之上》里写到,算法“通过奖励人性里某些基本本能,同时惩罚人性里某些善良的部分,而创造出了互联网喷子。”可以说,算法加持下的平台,早已背离了互联网出现伊始“整合信息”“让世界更加开放”以及“促进人与人的理解”等美好初衷。
尽管压力之下平台已经开始采取措施打击极端言论,比如处置违规内容、实施专项巡查,强化舆情监控等。但在流量依旧是平台主要利润来源的大前提下,这些措施顶多算是蜻蜓浮水、难触根本。
举例来说,某社交平台曾弹窗过这样一条信息,大意:奶奶戴上了外婆送给外孙的金项链,奶奶:“反正孩子还小用不上”。这是一条毫无营养的消息推送,但却隐含了可以引发争议成为“爆款”的诸多要素:婆媳矛盾、看孩子难题、传统习俗,乃至性别对立等等。因此,一个本来可能只是个体感受的表达,就有可能被放大,成为平台的流量密码。而一旦情绪被点燃,当事人随时可能成为被网暴的对象,而在现行的法律、规则等框架下,平台却完全可以全身而退。
这种推送符合平台盈利的逻辑,但却可能带来长久的、恶劣的社会效应。这种情况绝非只发生在中国,事实上,国外平台早已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21世纪初,Facebook进入互联网刚刚开放的缅甸,并很快成为该国民众首要的信息获取来源之一,因为算法优先推荐煽动性和情绪化的内容,该平台很快成为传播仇恨和虚假信息的工具,被缅甸一些民族主义者和军方利用来散布关于罗兴亚人的假新闻,加剧了针对这一少数群体的仇恨和暴力情绪,成为了2017年成千上万罗兴亚人被屠杀这一惨剧的间接推动者。
怎么办?加强社交平台审核义务是一个方向,但却并非良策。以上述某平台的弹窗为例,无论什么样的监管规则,都不可能禁止类似奶奶穿上外婆送给孩子金项链的信息传播,而若真的这样做,结果可能是掐断了信息的流动,恶果更甚。要求平台承担社会责任,也只能是一个道德准则,在现有盈利模式上难以上升为其行为规范。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三位得主中的两位——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与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提出了一个极富想象力的解决方案——对平台征收高额数字广告税。在今年3月在一篇题为《对数字广告征税的迫切需要》的文中,他们呼吁这样做是为了“鼓励其他商业模式,如基于(付费)订阅的模式,而不是目前内容免费、算法推荐、千方百计瞄准锁定用户的数字广告模式。”
“我们陷入了一个糟糕的状态,就像当年45%的成年美国人吸烟成瘾一样,人们此后花了几十年时间才戒掉烟瘾。”两位作者写到,“内容免费、基于广告的社交媒体会让人上瘾,然而对个人和社会极其有害,就像吸烟一样。” 近年来,随着大模型推动人工智能发展进入快车道,对数字广告征税的必要性进一步凸显。他们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会进一步提高个性化数字广告的变现能力,从而加剧有害内容的传播。
这是应对平台外部性的一种创新思路,但是否可行还面临争议。反对者担心这可能是抑制平台创新,也有人认为除非能达成国际合作,否则难以落地。但无论如何,监管还是可以有所作为。
一些媒体从业者也在行动。曾供职于《赫芬顿邮报》的美国记者Isaac Saul深感政治极化之痛,创建了一家独立新闻网站Tangle,其做法是,针对关键新闻首先会展示各党派的相关看法,最后由编辑以中立的方式总结。该网站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广告,只通过付费订阅模式运营,尽管其受众规模目前仍然有限,但至少是一个有益的尝试。类似的还有一些“事实核查”网站的兴起。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授胡泳在一次内部讲座上提出了一个他认为的终极的解决方案:鼓励用户用脚投票,离开平台。但这注定是个漫长的过程。只有吸收足够的雨露——来自学界的理论共识、舆论界充分的讨论、用户媒介素养的培养,等等——竹笋才能破土而出。在这之前,钟睒睒怕是很难等来张一鸣的道歉,即便等来了,也改变不了下一场、以及下下一场网络风暴正在无休止酝酿的现状。
版权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
本文系作者授权百度百家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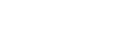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