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乌克兰,基辅(美联社)——在这里,他就是Alya Shabaanovich Gali,一个很受欢迎的医生,有一排病人等着看他。对远在数千公里外的家人来说,他是阿拉·沙巴安·阿布·加利,那个离开的人。
在过去的30年里,这些身份很少有融合的理由:加利在加沙的不稳定中离开了,在基辅定居了下来,为了更符合当地的语言,他取了一个不同的名字,娶了一个乌克兰女人。通过电话,他与在加沙的母亲和兄弟姐妹保持联系。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生活是平行的。
2022年2月,空袭和导弹袭击使加利的生活陷入混乱。将近20个月后,他把家乡变成了地狱,举家背井离乡。
两者都是暴力冲突,打破了地区和全球的权力平衡,但随着它们的爆发,它们似乎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乌克兰在痛斥盟友的同时,自己的军队却在前线苦苦挣扎。巴勒斯坦人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在每个地方,猛烈的轰炸和激烈的战斗摧毁了整个城镇。
在加利的生活中,战争汇聚在一起。一个月前,他的侄子在以色列的一次空袭中丧生,当时他正在觅食。几周后,一枚俄罗斯导弹炸毁了他工作了大部分职业生涯的私人诊所。同事和病人死在他的脚下。
“我在那里经历过一场战争,现在我也在这里经历一场战争,”48岁的加利说。他站在医疗中心被挖空的厢房里,工人们正在清理玻璃和碎片。“我的心和思想的一半在这里,另一半在那里。
“你和你的家人在巴勒斯坦目睹了战争和破坏,在乌克兰亲眼目睹了战争和破坏。”
加沙到基辅
有一句阿拉伯谚语形容一个家庭最小的孩子是“最后一颗葡萄”。加利的母亲会说,最后一个才是最甜蜜的;他是10个孩子中最小的,也是她的最爱。
加利九岁时,他父亲去世了。当时经济拮据,但加利在学校成绩优异,在看到亲戚们难以怀孕后,她梦想成为一名专门研究生育的医生。
1987年,第一次巴勒斯坦起义,或起义,在加沙和。早在法塔赫扎根之前,加利就加入了法塔赫运动的青年组织,这是一个支持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政党。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被逮捕和审讯;一些人进了监狱,另一些人拿起武器。
加利有一个选择:要么留下,冒同样的命运,要么离开。
有个好消息:一个去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学习医学的机会。加利含泪向家人告别,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他们。
他去莫斯科旅行,希望能赶上火车。相反,他得知阿拉木图不再是一个选择。但在基辅有一个地方。
1992年,年轻的加利来到乌克兰,当时苏联刚刚解体。
他说,这就像从一个疯人院转到另一个疯人院:“这个国家处于混乱状态,没有法律,生活条件非常困难。”
许多同行离开了。加利留了下来,进了医学院。
新生活,新名字
在乌克兰语中,没有对应的阿拉伯语声门辅音。所以在基辅,Alaa变成了Alya。他取了一个父姓的中间名,在他父亲的名字后面加上一个常见的后缀——沙巴诺维奇。
在学习俄语(大多数生活在苏联统治下的乌克兰人都说俄语)的同时,加利还在为办事而挣扎。邻居们帮助。通过他们,他认识了他的妻子。他们将有三个孩子。
他从医学院毕业,成为一名专门研究生育的妇科医生。他的职业生涯早期很长,见过几十个病人。最终,他在阿多尼斯医疗中心实习,并在那里茁壮成长。
当加利听着阿拉伯语歌曲开车去上班时,他会经过基辅的独立广场,那里是反政府抗议活动的舞台。他记得那年加沙也发生了一场战争。
随着乌克兰街头标语的呼啸而过,加利口里唱着歌词:“你一直在碾压我们,哦,世界。”
战争发生碰撞
7月8日,加利在工作,但他的心思在加沙。
一个星期前,一位亲戚联系了加利,他12岁的侄女在以色列坦克推进到拉法西北部为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设立的马瓦西营地边缘时丧生。像成千上万的加沙人一样,他的家人在以色列将其定为加沙地带后步行到了那里。
加利已经在哀悼了。他的侄子法特希(Fathi)上个月被杀。加利说,他是在电视上亲眼看到的——他侄子毫无生气的尸体出现在屏幕上,新闻标题用阿拉伯语闪烁着。他向一位亲戚描述了这张照片和法特希的衣服,后者证实这就是他。
他们的死亡给加利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在美国,他一直生活在对家人的恐惧中,害怕收到一条短信说他们都被杀了。
那天,在医疗中心,空袭整个上午都在响。在问候下一个病人之前,他和中心主任说了几句话。她告诉他,几个小时前,她刚刚被导弹击中,乌克兰最大的儿科设施变成了废墟,这是一个可怕的景象。他告诉她他侄女和侄子的死亡,以及他悲伤的黑暗。
不久之后,加利的世界变得更加黑暗。
一枚俄罗斯导弹冲向中心,引发爆炸,炸毁了三楼和四楼。
加利在第四天工作。在浓密的废墟中,他找到了满身是血的影子。他看到了一个病人,用手机照明,把她从倒塌的屋顶下拉了出来,而他周围的同事和其他人都死了——总共有9人死亡。
他把这名妇女带到他的办公室,等待救援人员。在地板上的尸体中,他发现了一名同事维克托·布拉古萨(Viktor Bragutsa),他流血不止。加利没能救活他。
一个存放病人文件的房间被夷为平地,他们几十年的记录在烟雾中消失了。
他感到一种似曾相识的痛苦。
几个月来,他看到了加沙战争的画面。就好像他们不知何故渗入了他在乌克兰的生活。
“没有什么是神圣的,”他说。“杀害医生,杀害儿童,杀害平民——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局面。”
只有痛苦
两周后,加利站在同一个地方,看着被炸坏的墙壁,工人们在废墟中搜寻。“我能感觉到什么?”他说,“痛苦。”没有别的。”
中心主任办公室被毁。接待区也是。超声波机和手术台杂乱无章地摆放着。
他一直呆在乌克兰,没有撤离他的家人——他在办公室里寻求安慰,帮助病人。他还说,他会留下来。
他知道,在加沙,他的家人没有安全的地方。
由于通讯中断,沟通并不容易。几周过去了,没有任何消息,直到一个侄子或侄女发现了足够的信号,告诉他他们还活着。
“无论情况多么困难和不可能,”他说,“他们的话语中总是充满了欢笑、耐心和对上帝的感激。
“我在这里,感受着它的重量。”
版权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
本文系作者授权百度百家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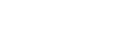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