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旧称“渝州”,自隋开皇九年(589)起,到宋崇宁元年(1102)结束,前后有五百多年的历史。渝州作为正式的行政地名终结于崇宁元年,这一年朝廷将渝州改名为恭州。至于改名的原因,由于史无明文,所以后世谈到这个问题时便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渝州”作为行政地理名称是在北宋结束的,但作为一个地名代称却一直被广泛使用,今日重庆的简称还被习惯性地叫作“渝”。可见“渝州”使用的时间虽然不如“巴郡”和“重庆”长,但对于这个古称的历史记忆,并不会因为它比另外两个使用超过八百年的名称时间短了许多而有所褪色。然而历经隋、唐,持续了五百多年的渝州,何以会在宋代被朝廷废弃不用?
一
宋代的重庆,主要沿袭隋唐的渝州而来。宋初灭后蜀统一四川后仍为渝州,按唐制渝州辖有巴县(治今重庆市市区)、江津(治今重庆市江津区几江街道)、万寿(治今重庆市永川区朱沱镇)、南平(治今重庆市巴南区双新村)、壁山(治今重庆市璧山区)五县。入宋后在乾德年间(963-968)将万寿县并入江津县,雍熙年间南平县并入江津县。庆历年间朝廷又将南州(治今重庆市綦江区)、溱州(治今重庆市綦江区青年镇)两个羁縻州划属渝州。熙宁七年(1074)此二州划出,单独设置南平军(治今重庆市綦江区),至此渝州辖县固定下来,即辖巴、壁山、江津三县。崇宁元年,朝廷下诏改渝州为恭州。淳熙十六年(1189),又以宋光宗潜藩升为重庆府(喻意宋光宗一步到位地从恭王成为太子进而当上皇帝,是为“双重喜庆”),从此定名。

创造了“重庆”的宋光宗
重庆地处四川盆地东部平行岭谷、盆地中部方山丘陵和盆地南缘山地的交接地带,在自然条件上与富饶的成都平原有着巨大的生存差距。由于环境恶劣,社会经济发展尚处在起步阶段,在时人眼中,重庆府的贫困与成都府的富侈形成鲜明对比。南宋中后期曾任重庆知府的度正感到重庆居于“夔峡之间,大山深谷,土地硗确,民居鲜少,事力贫薄,比东西川十不及一二”。尤其是渝南地区,由于地形上处于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的交接带,往往是深山峻岭,土地尤为贫瘠,“萆山硗确强田畴,村落熙然粟豆秋”。南宋中期游宦路经恭州的范成大对此地的感受是“盛夏无水,土气毒热,如炉炭燔灼。山水皆有瘴而水气尤毒”。
瘴,即唐宋时代南方山区客观存在的一种区域性病毒,在社会生活中,它夹杂着唐宋士人对落后地区的恐惧想象;同时,瘴的分布在政治上反映的是中原王朝势力在南方民族地区的影响力和民族地区为中原文化所涵化的深浅程度。大山深谷阻挠的不只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也阻挡着中原势力在这一地区的进一步深入。重庆在宋人印象中是“地势刚险”,人民“重屋累居”或者“结舫水居”(今天重庆的著名网红景点红崖洞还仍然保留了这些特色),这是一种大异于中原的景观。伴随着这种景观,这里的人民“刚悍生其方,风谣尚其武”,这是一种明显的落后性的暗示。

重庆的网红景点红崖洞
事实上,宋代重庆地区的社会经济的确不发达。在这里,官府能够控制的户口相当稀少,西川的成都府在北宋后期登记户数达18万之多,东川的梓州稍差一点也有10万多,而渝州只有4万。可见度正的“比东西川十不及一二”略有夸张,但也离实情不远。
南宋后期成书的《方舆胜览》在开列已改名重庆府的渝州的骈文惯用语时,说的是“有易扰难安之俗,多欺孤负弱之奸”,又“盛跻容而剽锐气”,可见此地难治的印象已经沉淀下来成为一种风俗的象征性符号了。孔子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泰伯篇》)渝州有这样的意象,在当时自然也就成了仕宦之人的畏途。对不少人来说,到渝州做官就颇有些不情愿,鄙视当地的风俗也就成为当然,当年苏轼所拟燕若古知渝州诏书是这样说的:
巴峡之险,邑居褊陋。负山临谷,以争寻常。独渝为大州,水土和易。商农会通,赋役争讼,甲于旁近。毋以僻远,鄙夷其民。
宋人对渝州风俗的看法恰恰也印证了“乱邦与危邦”的意象。这道诏书虽然有夸赞渝州的话,但仔细体会其中流露出的,竟有一种这地方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味道,末了还要特别提醒一句“毋以僻远,鄙夷其民”,则更是表明这里常常被鄙夷。以致宋哲宗时知渝州的王叔重仅仅“在渝州不夷陋其俗”,就要让时人吕陶对此大加赞叹了。于是,但凡到渝州做官的,友朋送行之时写上几句让赴任者聊以自慰的诗句也就是常事了。
“歌将听巴人,舞欲教渝童。况常善秦声,乐彼渝人风”,这是梅尧臣给将去渝州上任的张先写的送行诗。诗句从表面看来还相当欢愉,体味一下,背后却暗藏着这种欢快只是因为这里的异域风情恰与当事人的爱好相合而聊以自慰罢了。要是把宋人渝州为官的心情拿来和元人的由衷之喜对比一下,就更能体现出宋人并非心甘情愿。元人范梈在给其将到重庆做官的朋友的诗中写道:“干戈何草草,只说渝州好。但得渝州官,甘就渝州老。渝州古雄城,彭君旧建旌。至今江石上,犹有古时名。”渝州具备的雄城名镇的元人情感,表明元代的渝州意象已与宋人大异其趣了。
二
杜甫流寓巴蜀时写过一首绝句,“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考诗中所讲“杀刺史”的历史事件,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俱不载,详情我们今天已不得而知。南宋黄希在《补注杜诗》中说此事本末如下:
鲍曰:《崔宁传》所书山贼也,前年渝州杀刺史,谓段子璋陷绵遂。今年开州杀刺史,谓徐知道之反,有乘乱者。开去成都远,不知其故,史不书,失之。
师曰:步将吴璘杀渝州刺史刘卞以反,杜鸿渐讨平之,又部卒翟封杀开州刺史萧崇之以叛,杨子琳讨平之。
考鲍文虎所注“段子璋陷绵遂”事,在肃宗上元二年(761),史载:“(四月)壬午,梓州刺史段子璋反,子璋骁勇,从上皇在蜀有功,东川节度使李奂奏替之,子璋举兵,袭奂于绵州。道过遂州,刺史虢王巨苍黄修属郡礼迎之,子璋杀之。李奂战败,奔成都,子璋自称梁王,改元黄龙,以绵州为龙安府,置百官,又陷剑州。”同年五月,乱平。“乙未,西川节度使崔光远与东川节度使李奂共攻绵州。庚子,拔之,斩段子璋。”而徐知道之反在第二年,即宝应元年(762),史载:“(七月)癸巳,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反。”但作乱不及一月,“(八月)己未,徐知道为其将李忠勇所杀,剑南悉平”。可见鲍注尚合大节,但渝州、开州之事的细节已不得而知了。
而师古注所云之吴璘、刘卞、翟封、萧崇之四人名字,两《唐书》及《资治通鉴》俱无一言提及。不知注中所言所据何书?且杜鸿渐于大历元年(766)入蜀为西川节度使,因惧崔旰之逼,“日与将佐高会,州府事悉以委旰”。而杨子琳于大历三年(768)举兵作乱,围攻成都,次年战败沿江东下,经涪州至夔州,其中当路过开州,然杨此时本身即为叛贼流寇,注中其讨贼之说恐不足信。
清人钱谦益对此注则径直断为伪言欺人:“天宝乱后,蜀中山贼塞路,渝开之乱,史不及书,而杜诗载之。师古妄人,因杜诗而曲为之说,并吴璘等姓名,皆师古伪撰以欺人也。”则此注虽然时间、地点、人物俱全,但其中细节亦颇为可疑。
此事在常见的两《唐书》及《资治通鉴》等史料中都无记载,宋人作注欲推言此事的详情,也是多凭猜测。问题的关键也就在此,对于这么一个史已失载的事件,只因杜甫诗中偶然提到了渝州,宋人就以此诗为渝州人好作乱的明证,时人也对此津津乐道,这就不得不引人深思。
活跃于南宋中期的吴曾在《能改斋漫录》中讲述北宋末年渝州人赵谂因谋反伏法的事,同时不无感慨地说:“然渝州风俗,从古如此。杜诗:‘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此其验也。”体味杜甫此诗的原意,恐怕只是为了表现时局的动荡而抒发他漂泊无依的心情,未必有“杀刺史”之地便是乱邦的弦外之音。试想州县叛乱之事,史书之中何代无之,又何地无之呢?吴曾竟用“前年渝州杀刺史”来证明渝州好作乱是风俗如此,恰恰说明在他那个时代,渝州好作乱的名声已经深入人心了,才会出现这么一个把杜甫本意为时局动荡的诗,在指向上做出如此偷梁换柱式误读的奇怪现象来。
赵谂谋反在渝州被弃用的问题上关系重大,南宋王明清为当年牵涉赵谂事件的宰相曾布(1036-1107)的外家子孙,其先人曾抄有曾布当年谈及此事的节本,对此事当最为明白。王明清在其所著的另外一部笔记《玉照新志》中对此事所言甚详:
赵谂者,其先本出西南夷獠,戕其族党来降,赐以国姓。至谂,不量其力,乃与其党李造、贾时成等宣言,欲除君侧之奸,词语颇肆狂悖,然初无弄兵之谋。建中靖国时事既变,谂亦幡然息心,来京师注官。时曾文肃当国,一见奇其才而荐之,擢国子博士。谂谒告,省其父母于蜀中,其徒勾群以前事告变,狱就,遂以反逆伏诛,父母妻子悉皆流窜。改其乡里渝州为恭州,文肃亦坐责。
“乱邦”与“危邦”是宋人对渝州的想象,但这种想象绝不是毫无根据的臆想,而是在宋人既有的渝州知识基础上,通过内在思考而显现出来的。宋人所接受的渝州知识,是把渝州当作一个蛮荒之地的异域形象来记述。宋初的《太平寰宇记》讲到渝州风俗时特别强调了这里的“异”的特质:“大凡蜀人风俗一同,然边蛮界,乡村有獠户,即异也。”到了南宋,诗人范成大路过已改名为恭州的渝州时也被这里的“异质”性所吸引:“翠竹江村非锦里,青溪夜月已渝州。小楼高下依盘石,弱缆西东战急流。入峡初程风物异,布裙跣妇总垂瘤。”
《太平寰宇记》在点出渝州“异”的特质后描述了散居在这里的西南少数民族的生活状态,“今渝之山谷中有狼猱乡,俗构屋高树,谓之阁栏,不解丝竹,惟坎铜鼓,视木叶以别四时,父子同讳,夫妻共名,祭鬼以祈福也”。此外,经过上千年的沉淀,渝州地区在风俗上迥异于中原礼乐文明的“巴渝舞”仍被持久关注,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人们在渝州知识的异域特质下所做出的选择性记忆的结果。王应麟在《玉海》中回顾了《晋志》《隋志》《唐志》等典籍对巴渝舞的记载,巴渝舞的来历是汉“高祖初为汉王,得巴俞人趫捷善斗,与之定三秦、灭楚,因存其武乐。巴俞之乐自此始”。因它是一种武乐,所以更多的体现出了当地人的天性劲勇和剽锐之气。这无疑又会反过来加深它异域的形象。

现代人表演的巴渝舞
北宋中后期做过渝州知州的王叔重发现他所治理的地方,还是一个尚未被华夏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开发”的蛮荒之区,他在这里为官所做的工作正是文明开化的工作,他“葺乡校,集诸生,躬自课试,以补不学少儒之弊。置医生,审方剂,督察诊疗,以救尚鬼不药之死”。此外,宋人流传的前代在渝州发生的神异故事,也多少说明了这里的蛮荒异域形象已进入宋人的知识结构。仅《太平广记》就记载有《牙将子》《渝州莲华》《仙池》《渝州滩》《碧石》等五个发生在渝州的神异故事,人类学的相关研究认为:“蛮荒的地域环境容易滋长出神秘主义的价值取向与非理性的情绪。”由此反推,人们相信神异故事能够发生在这个地方,表明他们的意识深处这里就是所谓的蛮荒异域。
三
渝州这种“异”的特质的形成似乎与它靠近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南平蛮就世代居住于渝州附近。同时,作为汉人聚居区与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边缘地带,渝州常常反复出现戎汉之间的冲突与交融。程师孟“提点夔路刑狱,泸戎数犯渝州”,张商英“调通川主簿,渝州蛮叛,说降其酋”,而辛有终“治平二年(1065),知渝州。州界滨带獠夷,种人喜乘间内侵,捕吏平居未尝撤警”。可见,冲突频繁到已需随时预警的地步。最大的一次冲突则是神宗熙宁年间以南平军的建置为结果的李光吉之乱。这次冲突激烈,前后反复,相持达数年之久。
渝州的异域形象与长期戎汉竞争的背景,自然会让官方产生“异域”必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疑虑。而长期的戎汉竞争又使这里绝非安全之地,由此让人觉得这里是好犯上作乱和危险的地方也就不足为怪了。有别于中原的异域形象,宋人“乱邦”与“危邦”的渝州想象的知识基础,加上长期戎汉相争的事实背景,不得不对异域的渝州产生“乱”与“危”的忧虑,这就是渝州意象的全部内涵。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再来解读宋人对“渝”字的敏感,以及重新审视渝州的易名,自然就豁然开朗了。
渝州的异域形象与长期戎汉交融的背景形成了宋人“乱邦”与“危邦”的意象,这一意象反过来又会加深对作为异域的渝州的忧虑。赵谂事件的发生在时人看来正好印证了渝州“乱邦”与“危邦”的意象,证明了他们对异域的渝州的担忧不是杞人忧天。汉字的特殊性就在于它作为地名标记符号时,仍会让人联想到符号本身每个字的意义。“渝”字的意思是“变”,变就意味着对朝廷有异心,有异心就意味着要犯上作乱。于是渝州这个名字就成了一个刺激他们对“乱邦”与“危邦”忧虑的符号,导致朝廷在赵谂事件后的第二年做出了把渝州改为恭州的举动。
正如前揭《能改斋漫录》中吴曾吐槽的“渝州风俗,从古如此”那样,宋人普遍认为赵谂这样的乱臣贼子的出现与渝州自古风俗不够纯良有直接关系,出一个赵谂这样的“坏人”并非什么心腹大患,渝州地方充斥的边鄙危乱习气才是朝廷的心头刺。赵谂作为渝州地方乱邦与危邦的异域文化特质非常有冲击力,其父赵庭臣本为渝州当地少数民族南平僚的某部酋长,据《能改斋漫录》所记,赵庭臣曾与当地部落首领一起盟约归降朝廷,但他却使诈“醉诸酋杀之,扬言众叛,掩为己功”,可见赵谂与其父在时人看来,皆是凶狠险诈之人,渝州有此风俗,赵谂最后做出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也就不是个人品质问题而是地方风俗问题。
不过,宋廷最后用“恭州”替换渝州,恐怕也只是一厢情愿的文字游戏,渝州易名恭州的背后,真正的动因可能是朝廷试图通过“易名”的方式对渝州进行一次移风易俗的改造,尽管这种改造应该并无任何实质意义的行政资源的投入,纯粹是一种“口嗨”,即将“恭州”之名宣示天下来表达一种变易渝州地方恶劣风俗的意愿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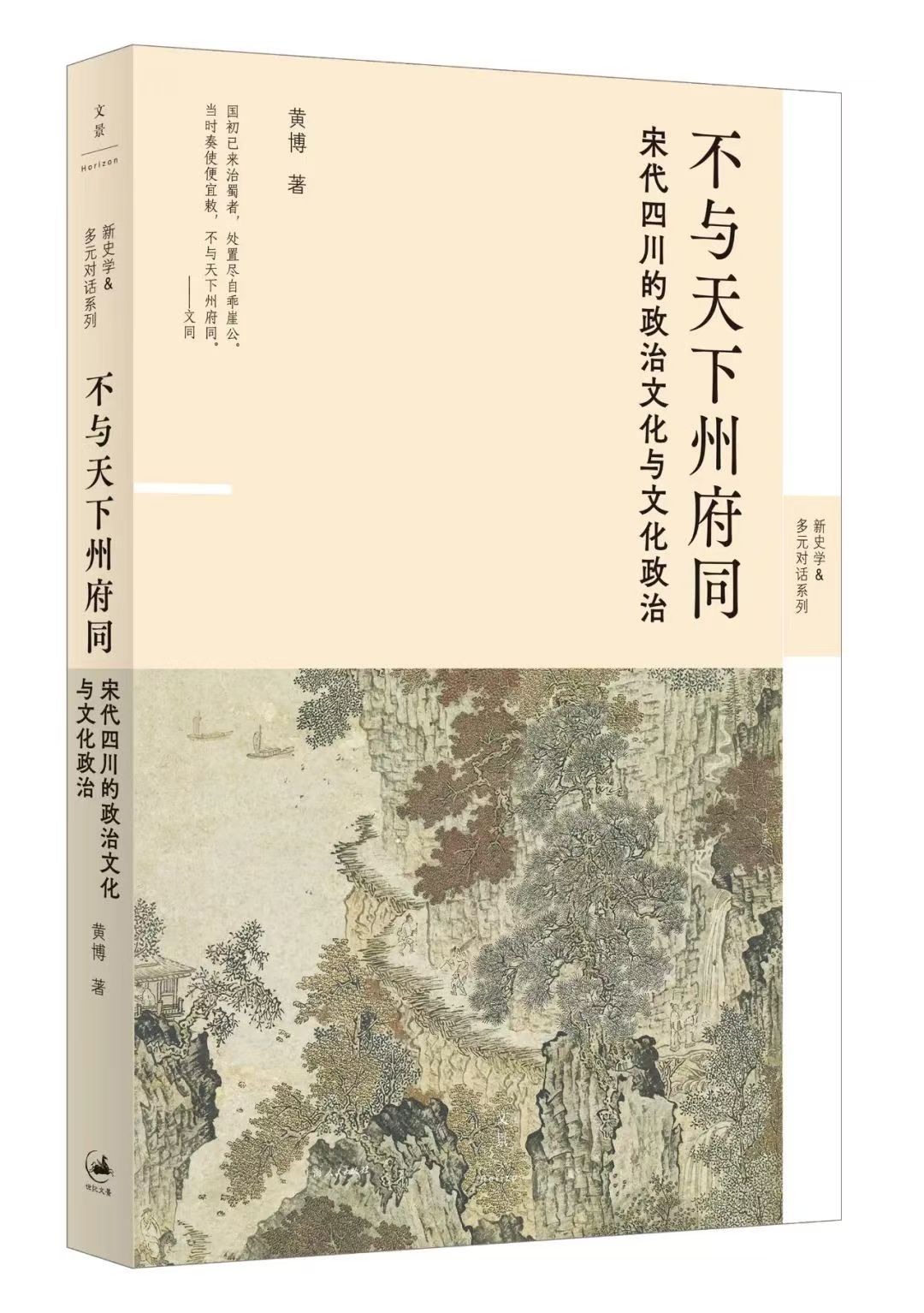
(本文摘自黄博著《不与天下州府同:宋代四川的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10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作者对原文做了部分修改。)
版权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
本文系作者授权百度百家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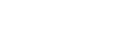











评论